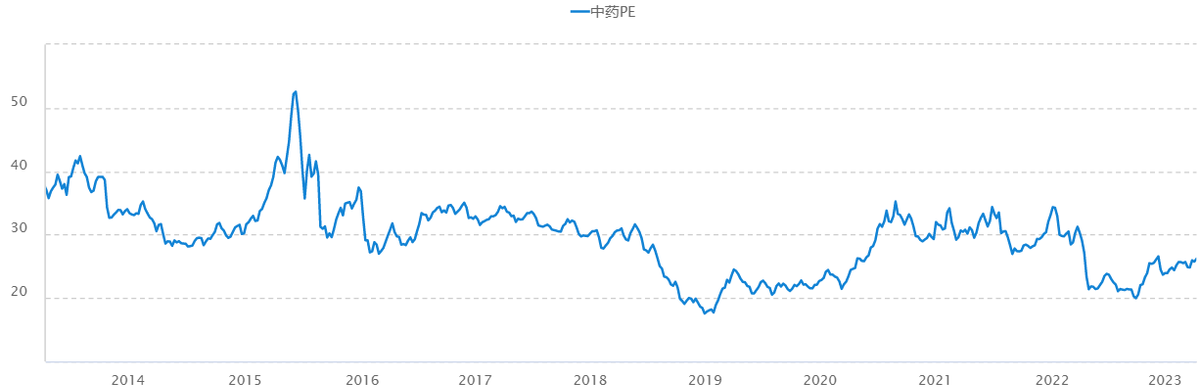如何高质量地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把脉中国经济)
其次,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9.75万亿元,但存款却增加了22.48万亿元,增加的贷款又流回了金融机构。目前MLF的利率为2.5%,1年期、5年期以上的LPR分别为3.45%、4.2%,均为历史最低水平。但10月份CPI和PPI同比分别下降了0.2%和2.6%。CPI今年同比一路走低,增长率从年初的2.1%下降到了10月份的0.2%;PPI更是连续13个月同比负增长。
首先,提高储蓄率,进行大规模基建和住房投资,是政府增长经济常用且比较容易把握的方式,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或衰退期,这种方式在短期确实取得过不错的效果,甚至创造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依靠大规模投资和资本扩张,德国和日本1948-1972年人均产出分别达到了8.2%和5.2%,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及之后的近三十年里实现了GDP总量每年超7%的高速增长。但是,提高储蓄率,进行大规模投资和资本扩张,对长期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不能长期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某个时期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收敛。德国和日本1981-2021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62%和1.70%;美国、英国和法国1991-2021年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2.43%、1.71%和1.45%;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2000-2021年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放缓至3.02%、6.28%、4.65%和3.38%。高速增长后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其增长速度放缓是很难避免的魔咒!
最后,制度变迁依然是我国经济高质量稳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和基本保障。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只有当制度能够为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提供有效的激励与保障时,持续性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才会发生。始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我国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其中,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20%。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变迁依然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节奏,积聚了很多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产权关系还不是很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政府的治理结构还有待于完善,分配格局还达不到经济增长的要求,市场主导地位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有时还很不到位等等。
(本文作者李锐,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三、审慎地运用政策工具
从1956年开始,我国政府增长经济的主要方式是大规模投资和资本扩张,不少年份的投资甚至超过了GDP的50%,这种长期依靠高储蓄率来快速增长经济的模式导致了整个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在某个历史拐点,其增长速度自然会缓慢下来,恰逢三年疫情使这个转折点提前到来了。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我国GDP持续9%以上的增长率将很难重现,4.0%-6.5%的增长率可能会是常态。理解并接受这一即将到来的事实特别重要,否则,我们调控和干预经济的决策和行为会扭曲和变形。增长率不应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毕竟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是每个人能够消费更多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享受更多的闲暇。
消费水平、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的应用和产业链的扩展、制度变迁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基本盘、驱动力和根本保障。
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巨额贸易顺差是其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的表现,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应该是贸易进出口大体平衡。一般来说,出口会使国内消费者的福利受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四十年,但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提高的速度都远不及经济增长的速度,长期巨额贸易顺差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把净出口视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会受到生产要素的成本和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化的约束,并且长期巨额国际贸易顺差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偏离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最终会难以为继。可以预计我国的国际贸易顺差未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是在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相互激励下取得的,如果没有相适应的制度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难发挥出来,譬如,如果没有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大量个性化定制产品的需求和生产要求有更加清晰和完整的产权制度的激励。展望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制度变迁相互激励相容完全有可能再度创造出经济增长的奇迹。
要避免因为就业压力而“开技术革命历史倒车”的行为,我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应该始终与有效率的技术革命相向而行。纵观历史,就业问题总能在每次技术革命拓展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中加以解决。
二、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形机器人的出现,未来至少80%以上的工作岗位可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毫无疑问,依靠人口红利增长经济的方式会随着技术的发展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很多人担心出生人口少了之后的养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大可不必杞人忧天!随着智能机器人和其他前沿技术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劳动力对GDP的直接贡献会越来越小。
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91.3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全年GDP的增长率有望达到5%。但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了0.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了2.6%,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引发了大家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担忧。
首先,提高消费水平是我国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只有当消费水平上升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维持经济的良性循环。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3%,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的占比分别为15.9%和38.4%;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万元,比上年实际下降了0.2%,远低于GDP的增速3%。同期,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72.0%,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分别为17.1%和54.9%;OECD经济体的平均值为77.3%,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分别为18.3%和59.0%;美国和英国在82%以上,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比达到60%以上;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分别为77.9%,67.8%和70.7%。很显然,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偏离了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采取高储蓄、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几乎是所有国家的选择。但是,依靠高储蓄率长期高速增长经济会使整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脆弱不堪。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后,无论怎样强调提高消费水平都不为过,消费支出的增加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基本盘。
最后,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拉动经济增长,一个功能完好的资本市场不仅是必选项,而且也是政府相对容易操作、成本最低和见效最快的政策工具。2023年二季度我国非金融企业未剥离城投公司前的杠杆率为167.8%,剥离后为93.1%,如此高的杠杆率掣肘了经济的快速恢复,一旦引发危机,后果会很严重。2022年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仅64.4%,主要受益于发达的资本市场。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能够通过投资人的买卖行为将优质企业识别出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其次,提高人口出生率,虽然短期能够增加经济总量,但人口出生率的上升不仅会减少商品和劳务的人均消费量,而且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由于生育周期较长,提高人口增长率在短期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其实也很有限。
最后,1994-2022年我国国际贸易一直都是顺差,2006-2022年每年的顺差都超过万亿元,2022年达到了惊人的5.87万亿元。2023年急转直下,前9个月国际贸易顺差只有3800亿元,预计今年贸易顺差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将会为负。
政府债务是“双刃剑”,过度举债会挤出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导致资本大量流出,资源配置严重扭曲,经济长期衰退,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高企,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性加剧,甚至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和动乱。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此类痛苦。我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普遍较高,到了必须下猛药治理的地步。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为21.4%,虽然还有一定的举债和减税的空间,但可操作的余地已不大。因此,我们必须审慎地运用财政政策的每一项工具,政策出台前必须首先充分评估其可能带来的最大损失。
(李锐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高春梅为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会计师)

目前中央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的空间已很有限,未来货币政策恐怕要肩负更多的重任。要使货币政策有效,其前提条件是要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恢复大家的信心,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使投资者能投资、敢投资、愿投资。
首先,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我国政府部门显性杠杆率为52.6%,加上城投公司负债的隐性杠杆率74.7%,广义杠杆率大致为127.3%。2022年末政府杠杆率美国约为135.0%,英国为101.8%,德国为66.2%,欧元区为91.9%,发达经济体平均为108.7%,G20国家为93.7%,新兴经济体为65.3%。很显然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已很高了。2020、2021和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分别为93.6%、105.8%和125.3%,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超过了150%;地方政府不仅举债数额大,而且成本高。今年10月中央政府决定增发1万亿元国债,财政赤字率将由3%提高到3.8%左右。
在我国股票市场上大约有2亿散户,其中账户资金量在10万元以下的占58.50%,在10万-50万元之间的占28.6%,这些散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都较高,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在股票市场上投资增加收入,将有利于扩大内需,驱动经济良性循环。但是,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目前绝大部分散户在股市上亏钱,决策层希望通过资本市场缓解企业债务风险的计划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了。
其次,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的应用和产业链的拓展是我国未来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和驱动力。我国很好地把握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在5G、6G和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我国已站在了世界的前列。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将我们从绝大部分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拓展出新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至少40%,整体经济提质35%以上;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将使我国GDP总量每年增长至少20%,对增长率的贡献可达1.0%-1.6%。
我国目前已进入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时期,面临国内外一系列复杂多变的问题和困局,应该审慎地运用政策工具,始终把提高全体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首要目标。
经济有自我恢复的机制,但过程非常漫长。政府常常会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
一、要正确地认识经济增长中的问题
目前有两种错误的认识值得重视。其一,认为消费没有乘数效应,依然应该通过投资和资本扩张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这种观点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无疑是正确的。但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和资本扩张近70年了,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最重要的阻遏因素,很多问题都与此相关!如果没有相适应的消费支出的增长,任何投资和资本扩张都将失去意义,同时也偏离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归宿。其二,过分强调进口国外的消费品。目前,还是应该把刺激消费需求的重点放在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上,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对国内产品和劳务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芝罘湾广场码头项目主体完工 “YT”型码头成烟台新地标
芝罘湾码头主体工程。大小新闻客户端11月28日讯(YMG全媒体记者金海善通讯员范文卿李子利摄影报道)昨日上午,工人师傅正在烟台芝罘湾广场码头进行护舷安装作业,这标志着芝罘湾广场码头主体工程完工,施工项目进入新的阶段。从空中俯瞰,以“烟台”两字汉语拼音首字母“YT”形状演变的码头与烟台山美景交相辉映,山、海、城、港融为一体,成为烟台别具一格的风景线,也将成为烟台又一新地标。大财经2023-11-29 15:21:290000南京邮电大学排名 南邮是一本还是二本
前往大学学习吧!那里有更加适合你的学习条件,也将带给你更多更大的平台来实现你的梦想,在这里也总是有很多的人会与你志同道合,进入这里学习也将是你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段旅程,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将给你极大的帮助,在这里学习你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与你相遇,勇敢去追吧!年轻的勇者们!第一档两所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第二档大财经2023-03-23 17:08:260000靠着比亚迪,深圳工业大逆转
文|江文华编辑|德利爱普生撤离。千万,不要让华为跑了!马斯克没有选择深圳,而是中意上海,在那里建了特斯拉超级工厂……这些话题,或许能反映出近些年深圳工业的最大挑战。然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2022年,深圳的工业增加值第一次超过了上海,一跃成为中国工业第一大市。图片来源:国民经略在劳动力价格上涨、房价地价高企、产业链外迁的当下,深圳的工业靠什么超越上海?大财经2023-06-16 23:08:320002结合2023年一季度业绩表现,选择今年的投资方向
恒瑞医药、伊利股份、隆基绿能一般来说,影响市场的只有两个因素,要么是业绩,要么是估值,而除了“中特估”这种特别情况外,业绩往往是影响股价的导火索,且是估值波动背后的一大因素。本着先选赛道,后选公司的逻辑,同时还要注重业绩表现,今天我们就从上市公司2023年一季报业绩表现来看看当前的市场,一季度业绩表现好的赛道尤其需要重视。在业绩可持续性基础上,一季度业绩表现好的赛道,今年的确定性会更大。大财经2023-04-29 22:32:420001